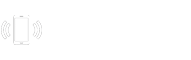劉火雄:出版機構(gòu)LOGO設(shè)計及其文化隱喻解析
作者:147小編 更新時間:2024-09-10 點擊數(shù):

原文刊于《中國出版》2019年第4期
摘 要:出版機構(gòu)的logo (商標) , 作為企業(yè)形象識別系統(tǒng)中的核心要件, 不但關(guān)乎品牌建構(gòu)和產(chǎn)品推廣, 其隱喻效果本身也是展現(xiàn)出版文化景觀的符號載體。出版機構(gòu)的logo設(shè)計多借用文字、動植物造型、畫作等元素來構(gòu)形、表情達意, 遵循原創(chuàng)、簡約、國際化等原則。
關(guān)鍵詞:出版; logo; 符號; 品牌; 文化;
伴隨微博、微信、客戶端等媒介的興起, 各類圖書工作室等涉足出版業(yè)務(wù)的機構(gòu)不斷誕生, 打造獨具特色的企業(yè)logo, 借以彰顯公司品牌形象、傳達理念愿景、提振傳播效力, 日益受到業(yè)界有識之士的關(guān)注和重視。無論基于出版實務(wù)考量, 或是從歷史維度來看, 經(jīng)典的logo設(shè)計既有一定規(guī)律可循, 也是企業(yè)文化建構(gòu)的題中之意。

一、視覺別體系與出版機構(gòu)logo溯源
現(xiàn)在通行的“l(fā)ogo”稱謂屬舶來品, 可追溯至“l(fā)ogos”“l(fā)ogotype”相關(guān)語詞, 它們涉及理性、活字、商標等義項。由于翻譯難免存在語義流失和轉(zhuǎn)換歸化的情形, 日常口語交際與文書寫作活動中, 外文logo的基本音、形、意被當代漢語所吸納, 如今已普遍約定俗成為商標、標識、徽標、社標等相關(guān)詞匯的代指。相較于理念識別、行為識別, 視覺識別無疑是企業(yè)形象識別系統(tǒng)中最直觀的內(nèi)容。視覺識別依賴于一整套組織化的視聽形象, 包括但不限于個性突出的logo、企業(yè)宣傳片、工作環(huán)境、辦公用品乃至員工的職業(yè)形象。logo作為視覺識別核心的構(gòu)件, 承載著公司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積累的使命。這也就不難理解, 許多出版機構(gòu)尤其是民營企業(yè), 特別注重在圖書書脊、封面等顯要位置印制公司或品牌書系的logo。
出版機構(gòu)logo的雛形, 與印刷技術(shù)的發(fā)明和推廣關(guān)系密切。15世紀中葉, 自德國的約翰內(nèi)斯·谷騰堡發(fā)明活字印刷術(shù)后, 歐洲迅速掀起了傳媒革命, 許多書冊上都可見帶有“十字架”和“天球”抽象圖案的組合標識, 借以體現(xiàn)出版方、印刷商的身份乃至宗教信仰。這些“印刷標志主要是承印工廠對于印刷質(zhì)量的一定承諾”, 同時“起著宣示‘版權(quán)所有, 不得翻印’的作用”。[1]中國古籍中的“牌記”兼具logo和版權(quán)頁的性質(zhì), 如著名的宋刻本《唐女郎魚玄機詩集》中, 便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印”題記;明末藏書家﹑出版家毛晉所刻印的典籍, 大多附其書齋名“汲古閣”字樣;武英殿皇家書局、金陵官書局等出版刻印機構(gòu), 也相應(yīng)標注“武英殿聚珍版”“金陵書局刊”類似牌記。
近現(xiàn)代以來, 出版機構(gòu)logo的演進, 與商業(yè)時代的勃興互為表里。19世紀末到20世紀前期, 上海四馬路一帶的“棋盤街”區(qū), 出版社、書店、報館林立, 數(shù)以百計, 為中國新聞出版活動的中心, 其中包括商務(wù)印書館、大東書局、大眾書局、申報館等知名機構(gòu)。為了保障自身權(quán)益, 在激烈競爭中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 除了書報刊出版、銷售等日常運營, 出版機構(gòu)的管理者大多重視企業(yè)logo設(shè)計和使用。如陸費逵主持設(shè)計并注冊了中華書局的logo:一本簡筆勾勒的典籍側(cè)立著, 封面上配以“中華”兩字的篆書, 古樸厚重, 圖書外圍由連接在一起的緞帶和麥穗環(huán)繞, 寓意同心協(xié)力、碩果累累。該logo較好地把企業(yè)名稱和營業(yè)范圍融為一體, 沿用至今 (見圖1) 。北新書局曾出版過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吶喊》《野草》、冰心的《春水》等文藝作品, 其logo為一本對開的書頁兩邊, 從右至左分別寫著“北”“新”兩個帶有魏碑筆意的美術(shù)字, 書本四周由寓示“光芒萬丈”的圓形圖案環(huán)繞。上述各具特色和寓意的logo, 成為出版機構(gòu)和出版物“身份象征”, 一定程度上便于樹立企業(yè)的品牌形象和強化讀者的認同感。此外, 后世學(xué)人在進行早年書刊版本考察時, logo同樣具備某些佐證價值。

圖1

圖2

第二、出版機構(gòu)logo設(shè)計基本形態(tài)與表征
出版機構(gòu)logo本質(zhì)上是一套符號系統(tǒng), 主要由圖案和機構(gòu)名稱組合而成, 有時會包括出版機構(gòu)名稱的外文翻譯 (或簡寫) 等元素。具象符號往往指向可感的物體, 抽象符號或者說符號的“象征”層面則更多地在于激發(fā)一系列認知、信仰和情感反應(yīng)。與中華書局、北新書局的logo一樣, 抽象的“圖書開本”作為基本構(gòu)形樣式, 時常被現(xiàn)當代許多出版機構(gòu)所采用, 如商務(wù)印書館、開明書店、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均可謂代表 (見圖3) 。這無疑是出版機構(gòu)主要社會功能的投射, 即主要從事書刊相關(guān)產(chǎn)品的研發(fā)、生產(chǎn)和經(jīng)營。

圖3
中文印章式出版機構(gòu)的logo在業(yè)界別具一格, 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故宮出版社、萬卷出版公司、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都賡續(xù)了中華傳統(tǒng)金石文化的流風余韻, 陰文 (或陽文) 篆刻古意盎然 (見圖4) 。與拼音文字通過字母進行線性排列組合不同, 方塊漢字自成格調(diào), 且大多旨遠辭高。正所謂“優(yōu)秀的視覺圖像形式之所以可能觸動人的情感心靈, 一定是形式中富含著人類的精神需求與意義感悟, 這是形意相生的核心要義”。[2]

圖4
不少出版機構(gòu)設(shè)計logo還會從圖畫素材中尋求創(chuàng)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現(xiàn)在的logo形象為三位勞動者揮鋤揚鎬的場景, 寓示著“開墾知識的處女地”, 其靈感主要移植于20世紀30年代蘇聯(lián)一幅名為《打擊懶惰工人》的宣傳海報。上海譯文出版社的logo則是一幅“乘風破浪”帆船簡筆勾勒圖案。日本幻冬舍的logo“據(jù)說是以見城徹本人為原型, 一個長發(fā)披肩, 腰圍布裙, 高高舉起一把標槍, 正要投向人們的野人剪影”, [3]看上去斗志昂揚、信心滿滿, 頗符合幻冬舍在日本出版界以“黑馬”姿態(tài)崛起的歷程。另外, “某些公眾使用的制作商標是由完全抽象而非類比性的圖形構(gòu)成, 但他們可能‘引起’與所指之間具有類似關(guān)系的某種印象, 這主要以一種潛在的類比性暗示發(fā)揮作用”, [4]如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旗下“理想國”品牌便是此類logo的范型 (見圖5) 。

圖5
隸屬于高校或大型集團的出版機構(gòu), 其logo多以對應(yīng)高校的校徽和母公司的商標來替代, 帶有鮮明的“借勢”傾向。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xué)校長期間, 請魯迅設(shè)計了校徽, logo中心“北大”兩字由三個人形圖案組成, 象征著學(xué)校乃育人之所。北京大學(xué)如今的校徽為魯迅創(chuàng)意的優(yōu)化版,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將其選作了logo的主要圖案。此外, 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劍橋大學(xué)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都采取類似方式 (見圖6) 。時下, 出版機構(gòu)logo設(shè)計常委托專業(yè)的公司進行, 但實際效果可能與預(yù)期存在較大差距, 受時間成本、經(jīng)濟成本等因素影響, 容易久拖不決, 在此情形下, 借用本校校徽或母公司的logo, 不失為備選方案。

圖6

三、動植物原型的文化隱喻
動物及其變體圖案在出版機構(gòu)logo中同樣普遍。企鵝出版社經(jīng)典的“企鵝”logo在業(yè)界耳熟能詳, 讀客圖書公司選取了憨態(tài)可掬“熊貓”作為logo的主要背景, 鳳凰出版集團的logo為一只寫意“鳳凰”。在人類的集體無意識當中, 歷來存在動植物圖騰崇拜的淵藪。例如鳳凰在東西方文化傳統(tǒng)中都有“涅槃重生”的隱喻, 在中國還有呈祥、尊貴的寓意, 獅、虎、豹帶有力量、勇氣、權(quán)威與復(fù)活等意指, 這在歐美紋章學(xué)中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 它們常被當作國家、貴族階層和權(quán)勢家族的圖騰 (見圖7) 。

圖7
在某些符號學(xué)專家看來, “全部人類經(jīng)驗無一例外地兜售一種以符號為媒介和支撐的詮釋性結(jié)果”。[5]動物符號種類豐富、形態(tài)各異, 在表情達意方面具備媒介優(yōu)勢。趙家璧、老舍等人民國時期開辦的晨光出版公司, 其logo便是一只昂首挺胸的雄雞造型。據(jù)《民國出版標記大觀》及其續(xù)集的作者張澤賢考證, 民國時期另有一家名為“晨光書局”的機構(gòu), 其logo主要元素包括雄雞、太陽和書籍:“一只雄雞站在三書疊起的‘高坡’上, 迎著旭日啼叫, 感覺到了聲響, 有著‘一唱雄雞天下白’的氣魄。”[6]英國泰晤士&哈德遜出版社以兩頭相互戲水的海豚作為logo, 很可能緣于古希臘人把海豚看作智慧和預(yù)言的象征, “在古希臘神話中, 海豚是眾神的信使、英雄的救星和靈魂前往福人島的護送者, 波塞冬、阿芙洛狄特、厄洛斯、得墨忒爾和狄俄尼索斯的標志”。[7]與此相仿, 中國國際出版集團旗下海豚出版社直接以一只騰空直立的海豚圖案作為logo (見圖8) 。

圖8
動植物原型作為賦予事物以象征意義的深層模式, 在歷史傳說、宗教中不斷積淀, 沿襲已久。如西方有些國家和地區(qū)把“樹”視為生命、健康和超凡力量的象征, 古人在樹林里祭神, 置身于高大的樹干和濃密的樹蔭中, 后來教堂的設(shè)計即模仿這種環(huán)境, 從詞源學(xué)上看, “真理” (truth) 和“信任” (trust) 兩詞派生自古英語“樹” (tree) 。[8]荷蘭愛思唯爾的logo正是一株纏繞著青藤的大樹 (樹下立著一位長者) , 借以象征傳播知識的出版商。譯林出版社的logo為三棵樹木的寫意圖, 這與“譯著成林”的取義頗為貼切 (見圖9) 。

圖9
為某套書系專門設(shè)置logo,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強品牌知名度, 進而便于與出版機構(gòu)logo結(jié)合生成集聚效應(yīng), 如春風文藝出版社的“布老虎”叢書、磨鐵圖書旗下“鐵葫蘆”系列、長江文藝出版社的“九頭鳥”叢書, 各有其特色。商務(wù)印書館打造的“漢譯世界學(xué)術(shù)名著”叢書, 封面上后來采用了象征散播思想、傳承知識的“蒲公英”圖案, 在業(yè)界學(xué)界口碑甚佳。

四、數(shù)字時代、經(jīng)濟全球化語境下的logo優(yōu)化路徑
出版活動兼具文化與商業(yè)多重屬性, 相關(guān)機構(gòu)的logo呈現(xiàn)出一般企業(yè)的共性, 同時蘊含某些特性, 專業(yè)化原則由此凸顯。logo符號通常帶有多層含義, 其象征意義與其說涵蓋了事物的整體, 不如說是指出了某種特性。對于專業(yè)性出版機構(gòu)而言, 設(shè)計體現(xiàn)核心主業(yè)的logo, 更容易讓讀者對企業(yè)有直觀的認知。如北京大學(xué)醫(yī)學(xué)出版社的logo采用了“靈蛇繞神杖”圖標, 這是古希臘神話中神醫(yī)阿斯克勒庇俄斯的象征, 聯(lián)合國世界衛(wèi)生組織、中國衛(wèi)生部均使用了該圖標。巧用出版機構(gòu)所在地的名勝古跡則有助于強化地域識別。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坐落于“秀甲天下”的桂林, 其綠色logo以拱形書籍為圖案主體, 造型與5A級風景區(qū)象鼻山相仿, 將書籍概念和當?shù)孛麆儆袡C融合, 清新而富有朝氣, 由啟功題寫的社名典雅挺秀, 相得益彰 (見圖10) 。

圖10
出版機構(gòu)的logo如果元素過于繁雜、堆砌, 非但不利于辨識, 還容易引發(fā)歧義, 結(jié)果適得其反, 注重簡潔性日益成為趨勢。特別是隨著社交網(wǎng)絡(luò) (微博、Twitter) 、智能手機、閱讀器等新興媒介以及數(shù)字閱讀潮流的興起, 簡明而富有意蘊的logo理論上更便于傳播和在電子媒介上呈現(xiàn)。如為了順應(yīng)互聯(lián)網(wǎng)數(shù)字時代的發(fā)展需要, 近年來哈佛大學(xué)出版社棄用了原來以校徽為模板的logo, 轉(zhuǎn)而采用新的logo, 即由簡單的6個紅色矩形 (上下各3個對稱排列) 組成了一個抽象的“H”符號, 形象地暗含了“書本書架”、“知識窗口”等寓意 (見圖11) 。

圖11
出版機構(gòu)logo的簡約風格與中國傳統(tǒng)的“留白”藝術(shù)異曲同工。使用圓圈、三角形、平行線等幾何圖案或純文字作為基本構(gòu)形, 容易實現(xiàn)logo的簡潔效果。“基本圖案一詞表示這樣一種功能:作為一種組織方式, 它給了藝術(shù)家的想象一個起點, 在一種極為樸素的意義上誘導(dǎo)著創(chuàng)作。基本圖案推動、引導(dǎo)著藝術(shù)品的發(fā)展。”[9]亞馬遜的logo以公司名稱和網(wǎng)址字母作主要元素, 極為簡約, 附帶的箭頭笑臉弧線, 從“a”指向“z”, 則象征企業(yè)始終如一的竭誠服務(wù), 其起源可上溯至《圣經(jīng)》中“我是阿爾法, 我是歐米茄”代表“開頭和結(jié)尾”的言論記載。這類簡約式logo在日本講談社、小學(xué)館, 美國麥格勞希爾教育出版集團同樣不乏示例, 它們以文字構(gòu)圖, 白底黑字或紅底白字, 尤其在電子閱讀屏幕上的即視感和沖擊力較強 (見圖12) 。

圖12
經(jīng)濟全球化的無遠弗屆效果, 促進了出版業(yè)的國際交流, 不同文明之間的融合乃至沖突均有程度各異的體現(xiàn)。對于有志于開拓國際市場的出版機構(gòu)而言, 如何尊重雙邊或多邊的文化差異, 設(shè)計出既能寄托公司理念、愿景又能被其他國家地區(qū)同道、讀者所接受的典型logo, 以期實現(xiàn)合作、共贏, 極可能是遲早需要應(yīng)對的議題。在擬用作logo的圖文元素中, 出版機構(gòu)尤其需要區(qū)別它們的接受語境和象征隱喻, 盡量入鄉(xiāng)隨俗, 而不至于陷入交流的無奈。因為logo符號的編碼與解碼過程使得意義得以被傳遞, 隨之產(chǎn)生理解、共鳴, 或引發(fā)誤讀、錯判, 這與特定的語境密切關(guān)聯(lián)。語境既是符號活動的社會條件, 又是物理性的指涉之物, 對于交流的發(fā)生起著決定性。符號活動的語境被組織為一系列文本, 參與者和關(guān)系等范疇都被賦予了意義, 信息制造者有可能把關(guān)于制造者、接受者和語境的明確規(guī)定納入各自的文本形式中。[10]如龍在中國常常是帝王、高貴、吉祥的典型象征, 在西方則往往代表必須克服的黑暗力量或障礙。成立于2010年的鳳凰阿歇特是中國出版業(yè)界第一家以國際資本合作形式組建的合資公司, 其logo外圍類似“H”構(gòu)形, 這正是法國阿歇特出版集團的logo, 內(nèi)部嵌入中文繁體“鳳凰”兩字, 整體呈現(xiàn)出典雅、莊重風格, 較好地融合了兩家出版機構(gòu)的特色。相比于動植物、宗教符號等圖案, 以數(shù)字、文字、幾何圖形為主要元素的出版機構(gòu)logo, 在國際化運營過程中通常帶有普適性, 較少引發(fā)歧義和爭論。江西二十一世紀出版集團的logo便融入了“21”和“C (即Century縮寫) ”的寓意, 同樣, 迪斯尼國際出版部的logo以其集團創(chuàng)始人沃爾特·迪斯尼的英文簽名為主要標記, 已深入人心 (見圖13) 。

圖13
時代、社會在發(fā)展, 人們的審美品位有時相應(yīng)會發(fā)生變遷, 并且企業(yè)經(jīng)營狀況、規(guī)模處于不斷波動中, 為此, 出版機構(gòu)的logo必要時需修訂完善、與時俱進。誠然, 具體在進行l(wèi)ogo設(shè)計時, 還需考慮色彩搭配、圖文協(xié)調(diào)、企業(yè)宣傳語放置等諸多事項, 這有賴于更多設(shè)計師、業(yè)內(nèi)人士等發(fā)揮創(chuàng)意, 從而為出版業(yè)增添新的文化景觀。
注釋:
[1]錢定平.logo的文化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141
[2]朱永明、鐘健.傳統(tǒng)漢字圖像藝術(shù)[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 2015:56-57
[3]傅月庵.得了編輯病的那個家伙![Z]都是愛書的人.華慧編.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3:162
[4][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學(xué)原理[M].李幼蒸, 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08:37-38
[5][美]約翰·迪利.符號學(xué)基礎(chǔ)[M].張祖建, 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2012:6
[6]張澤賢.民國出版標記大觀續(xù)集[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 2012:46
[7][8][英]馬克·奧康奈爾, 拉杰·艾瑞.象征和符號[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2014:162、212
[8][美]蘇珊·朗格情感與形式[M].劉大基, 傅志強, 周發(fā)祥,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 1986:82
[9][英]羅伯特·霍奇, 岡瑟·克雷斯.社會符號學(xué)[M].周勁松, 張碧, 譯.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2012:42
作者單位:
南京大學(xué)信息管理學(xué)院
版權(quán)聲明:本篇文章由朝夕友人官網(wǎng)小編編輯,僅限于學(xué)習(xí)交流,非商業(yè)用途,版權(quán)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來源標注錯誤或侵權(quán),請在后臺留言聯(lián)系小編,將及時更正、刪除。
上一篇:時隔15年,“百事可樂”換新Logo了! 下一篇:LOGO設(shè)計全方位指南
返回上一層